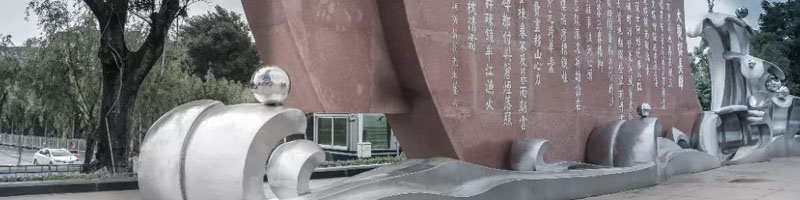栏目: 雕塑历史 中国雕塑史 西方雕塑史 作者:佚名 热度:
吴为山
历史以来,中国雕塑以两种存在形式最为显著:室内为佛教造像;室外为陵墓道前的石人、石兽。前者由于有严格的造像法限制和虔诚的宗教情感之制约,故大都合于法度,不似后者:超然、豪放、自在为之。也许是置于室外的缘故,若刻画得太实了,就失去了与天地争空间的雄强之势,所以古代大量的陵墓雕刻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自然形态,稍加雕琢,便神气活现,巍然磅礴。这种风格至汉代达到鼎盛。所憾的是汉代以降,此风渐减。至近现代,又因西洋雕塑传统的介入,中国雕塑大有以西方写实主义为体、为用的倾向,当代以西方现当代艺术为参照之势愈烈,故那种原本存在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写意精神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本文提出写意雕塑的概念,旨在强化与彰显,使“写意”在雕塑艺术中形成一股荡漾着民族之魂的新风。为此笔者就写意雕塑的特质、中国写意雕塑的背景、西方现代雕塑中的写意性以及中国写意雕塑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角色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写意雕塑的特质
“写意”,先有意,而后写之。
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意”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所涵纳的意义不尽相同。
雕塑乃至整个造型艺术中的“意”,与其他艺术门类中的“意”又存在更为明显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在于造型艺术之“意”是与“象”连在一起的,确切的说是“意象”。
“意”的因素使雕塑与理想贴近,“象”的成分,使雕塑与现实相联系。
这种“意象”的表现形式是“形”或“型”,它是创作者在综合了各种因素后,瞬间生成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超乎于现实之外,是作者对内心所生成“意象”的肯定。
写意处于写实与抽象之间,它既不会使人产生一览无余的简单,也不会令人有望而却步的深奥。它引导人们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心理作用之下,去把玩、体味、感觉艺术作品的整体及每个局部、细部的“意味”。智慧生成形式,写意凝固着瞬间感悟,凝固着生命激情,由于写意速度的迅捷,决定了它无矫揉造作,无“深思熟虑”,从而更接近于本质。当事物的本质与艺术家的精神高度对应时,艺术家在创造的过程中便自然地摒弃了表象的细节,抓住并突出客观事物中与创作主体相契合的那些特征来表现情感、抒发意兴。这就使得作品更趋于符号化并与感觉、理念融为一体,从而增强了其在空间、时间上的恒久性。所以,写意雕塑的特质,即是在雕塑中将人与事物之间的那种精神超越凝固化、物质化,而极富感召力。
写意雕塑中所注重的“意”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概念虽不尽相同,但也有着共通之处,故写意雕塑的发生发展亦有其在哲学、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深厚的文化背景。
二、中国写意雕塑的背景
(一)原始艺术的写意性
人类早期,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其艺术形式几乎相同,正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没有“你好”,也没有"HELLO"。
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导致原始人在表现技巧上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惟妙惟肖地刻画万物的表象,只能用心灵的触角去感受,也正是这可贵的一点造就了原始艺术中表现手法的高度写意性。因为感受的淳朴、直观、强烈,所以表现出的线条、体量以及生成的面与面之间的关系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一切虚伪的、一切技法层面的、一切苍白无力的伪饰荡涤得一干二净。即使在现代,由于某些地区民族的封闭,生活仍处于原始状,它们的艺术成了原始艺术的“活化石”。如非洲的木雕,中国贵州、云南地区的鬼魅文化雕塑等。但无论是远古时期的艺术抑或是现代社会的原始留存,他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写意特点:
1、究其一点,不及其余。突显客观事物的某一点,并理想化、神化。对一些特定局部进行重点刻画和不自觉的夸张。如刻画人时,最重眼之表现,或做成大球凸出,或凿成凹洞下陷。原始艺术中对眼部刻画的重视也是影响后来中国绘画理论中“传神写意,尽在阿堵中”(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之《风操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因素。
2、欲望性。欲望的专一性使他们在创作中去夸大某一局部而减弱其他。如夸大乳房、生殖器等,这在红山文化女体中有所体现,表现了原始人生殖崇拜心理。
3、情绪趋势。原始人在刻画事物时,受情绪的支配,收获的喜悦、狩猎的失败等都直接影响创作中刀痕的深浅、长短、力量。这是抽象表现主义的萌芽。
正是在这样一种多义与多功能的混沌性中,原始人以直觉塑造出了朴实的意象作品,足令后人叹服。
(二)哲学——从老庄思想中看写意
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寓言: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注:《庄子》之《天下篇》,中华书局。)
这则寓言指明用“理智”(知)、“思虑”(离朱)等并不能得到象征“道”的玄珠,而用“象罔”却可以。“象罔”即是有形和无形、虚和实的结合。就表现“道”而言,形象较言辩(概念、逻辑)更为优越。但这个形象并不单是有形的形象,而是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形象(象罔),老庄哲学也曾用“恍惚”(注:《老子》第二十一章,中华书局。)来形容“道”,所谓恍惚就是若有若无。尽管道包括“象”,道产生“象”,但是执着于孤立的有限的“象”却不能把握“道”。写意雕塑实则即是这样的一个结合体,即便从真人的面部、身体翻制模型,达到与之完全相同,它并不能称作为一个雕塑品,它只是一个有形的实体,必须与那无形的特质结合在一起,才能鲜活起来,雕刻家通过作品是要表达一种无形的内在东西,可称作为他要表达的“道”。要表达这种道,中国古代艺术家找到了与之相呼应的手法——写意。
王弼曾提出“得意忘象”(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一命题。它源自于庄子的“得意而忘言”。王弼提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即“意”要靠“象”来显现(意以象尽)。“象”要靠“言”来说明(象以言著)。但是“言”和“象”本身不是目的。为了得到“象”,就必须否定“言”,为了得到“意”,就必须否定“象”。这一命题启示我们审美观照往往表现为对于有限物象的超越。审美观照当然总是对于有限的具体的物象的观照。但是审美观照并不受这种有限的物象的局限,而是要投向宇宙、历史、人生。所以要达到艺术家所追求的“道”必须借助于有限具体的物象来完成,拘予写实则泥于具体物象的本身了。欲求之道恰如“水中之月”,近在眼前却掬之不得,而写意则是对这有限物象的一种超越,使作品获得无限拓展。
《中国艺术的意境论》曾提到中国的艺术意境理论是一种东西方超象审美理论。其哲学根基,则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注:蒲震亨《中国艺术的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整体的意境结构,表现为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动态审美。意境也不等于特定的艺术形象和典型,特定的形象是产生意境的一种母体;意境往往具有“超以象外”的特征,因此,意境具有因特定形象的触发而纷呈叠出的特点,它常常由于象、象外之象、象外之意的相互生发与传递而联类不穷。
(三)文学——从诗的角度看写意性
什么是诗?
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到:像一般艺术一样,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诗并不能把这变动不居、漠无边际的世相整体抄袭过来,或是像柏拉图所说的“模仿”过来。诗对于人生世相必有取舍,有裁剪,有取舍剪裁就必有创造,必有作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注: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什么是雕塑?
笔者在《雕塑的诗性》一文中曾有阐释:
雕的过程,就是删繁就简的过程,是减法,减得只留下筋骨、灵魂。
塑的过程就是添加的过程,是加法,加上原本属于作品的那部分。
雕塑就是推敲,过程无论是长是短,终是以一泻而下,或是以天然去雕饰而呈现。(注:转引自吴为山《雕塑的诗性》,《民族艺术》2001年第二期。)
诗歌的写意一方面重内容上写意: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另一方面也重形式上写意:格律诗是最讲形式的。新诗则讲究的是另一种更自由的形式,虽没有规律可循,却是浸入心灵的内在关系。如郭沫若《天狗》:
……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
……(注: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中,“我”的层层递进、加重,是语言形式的强调,他与诗人要奋争、挣脱、前进的意相吻合。
诗人写诗俱在表现一个“意”字,王夫之认为无论是诗歌还是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注:王夫之《 斋诗话》,中华书局。)
斋诗话》,中华书局。)
公安派袁中道提倡: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诗文之精光始出。(注: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上海杂志公司。)
明朝后七子之代表人物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提出:作诗妙在含糊,逼真反失奇观。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眺,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注:谢榛《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每一经典的诗都是一尊崭然的雕塑。同样,艺术史上那些写意性雕塑也都是一首诗。
(四)雕塑中的写意性
1、岩刻的意象——人与神的混合
人与神在先民那里往往是混同。神是虚幻的,无具体形态,而原始人欲在现实中找到神的对应形象,但又不甘以人表现神,便将许多幻想投射到人,而后便有了“神”,在表现上,他们把人瞬间最精彩的神采、势态刻画出来,作为对“神”的赞美,这种“转移”无疑是原始人观察力的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写意了。如西藏岩刻、连云港将军岩岩刻。
想象是创造的基础,但离不开人对客观事物的经验,因此,人神混合体现在造型上就是模糊的意象。先民受宗教情感的驱使,摒弃了自然事物的束缚,表现时可更多发挥,在情绪上较激烈,手法上较肯定,造型上更自在,所以这些作品往往成为神品。它们充分、饱满地发挥了作者的潜能。
2、汉代墓前“动物风格”的雕塑
秦汉是中国雕塑不断发展的时期,就文化传承而言,秦朝仍旧体现出战国时期秦国关陇一带平朴写实的特色,而汉朝则多承楚风,更具浪漫、夸张的成分。在雕塑风格上,秦朝追求写实逼真,汉代则讲求写意生动,并将这种风格推至高峰。(注:汝信《全彩中国雕塑艺术史》,宁夏人民出版社。)如汉代霍去病墓前石刻,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代表作之一的《马踏匈奴》表现了一匹昂首挺立的战马,安详而不失警惕,端肃中蕴涵着力量。粗壮结实的马腿,恰如四根巨柱,与马身浑然一体,古劲而朴拙。线、面、体相融的造型,增加了写的意趣、情韵,直抒胸怀。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东汉雕刻,是佛道并存的宗教题材,它反映了佛教初传中土之时,依附于道教以谋求发展的一段历史。作品已有一定程度的风化,但佛道互通的故事情节以及艺术风格,透过依稀可辨的形象仍可释读。卧、坐、立各种有机组合的姿态,人物比例及体量的高低凹凸浑然有致,利用山石的自然组合而生成有机的形式构成,人物的大小互补尽在淋漓写意中。
3、汉俑中的写意性
作为随葬品的俑,数量庞大,为适合成批模制的需要,工匠们在塑造时不得不舍弃对局部的精细刻画而毅然大胆的进行整体塑造。他们采取饱满的面,扁平的体,富有装饰意味的阴线和阳线,贯穿于作品,本来陪伴死亡的俑也赋予了快乐的生命。汉俑不似唐俑那样饱满圆润,表达的是自在、本然的生死观,创作者通过形式直达意念。
4、汉代的工艺铸件
汉代的工艺铸件通过夸张的动态表达意、趣。如“西汉盘舞”造型中线条的流畅性所呈现的律动感,犹如印度神湿婆造像的形式,且更加不注重形体的写实及细部的刻画,它着意的是形的整体流动关系,恰如书法运用线条构架而产生的节奏。
5、佛教雕塑
东汉永平初年,明帝夜梦金人,故遣使西域求法,由此,白马驮经西来,佛教之传播在中土以滥觞,佛教造像成为中国雕塑创作的主要题材,题材的性质限制了雕塑写意性的发展。佛教造像的要求高于一切,匠师们在创造佛教主要形象时,虔诚的心态只为塑造庄严的法相,法度减弱了艺术灵性。然而一旦他们塑造起供养人及影壁中那自由自在的云水、飞天,工匠们的心态便放松下来,而呈现出生活的世俗情感,佛像之外的“小人物”便被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往往这些不经意的塑造才是最具艺术性的。从许多遗存的作品看,可以分析这类作品在创作时速度快、轻松,具有高度的写意特征。衣纹的风格化倾向及人物非程式化神态的捕捉都积极影响着后代的雕塑。
概括言之,雕塑的写意,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形态的夸张意象,二是形体凹凸隐显的质感意象,三是人物瞬间神态的意象。
(五)民间美术
朴野的民间艺术是情、意的真切流露。较之于塑佛像的匠师他们更加畅快、无拘无束。正像民间口头文学那样,直接源自生活。泥巴的粘性在民间艺人手中生发出像他们对大地那样的热情,主客交融、意态百出、妙趣横生。一般地讲,面人多重线条般形体的流畅,瞬息万变而成形,泥人则重体面圆厚,常常是整体概括与精细刻画相对比而统一,久而久之产生程式。来自民间的智慧,其“意”是生命底层的涌动,是一个民族心理的基本结构所在,这是我们探究写意雕塑不可或缺的因素。
(六)绘画中看写意性
1、墓窟壁画
绘画的写意性,除史前洞窑壁画外,那些墓窟壁画在描绘人世故事与勾画升入天国的幻想时也总是以最简的线、最纯的色来表现,充满了乐观与轻松,油然而生意。甘肃博物馆所藏嘉峪关壁画便是典范,线条爽朗而悠游,造型只求神逸,超脱现世。
2、写意水墨
以水墨为代表的绘画更是体现了写意精神。意的表达甚至成为评判艺术之高下的标准。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对吴道玄评价甚高,曰:“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神假天造,英灵不穷。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他认为吴道玄的“离披点画”,风格更趋写意,故推崇备至。当有人询问:“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周者,谓之如何?”(“笔周”实为写实,“笔不周”乃指写意)张彦远最终对于写实与写意的评判是:“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己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注:钱钟书《七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可见,中国古人所追求的乃是笔可不周而意必周的中国艺术之写意精神!
绘画发展至董其昌,又分南北二宗,恰如禅宗之分南北,董其昌鄙弃耗人心力的北宗山水,主张意境恬淡的南宗绘画,实则是对中国写意精神之张扬。钱钟书在《七缀集》之《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提出,“南宗绘画的原则是‘简约’即以经济的笔墨获取丰富的艺术效果,以削减迹象来增加意境。”这个观点在于说明艺术家的创作要竭力摒弃表象的细节去获取意的恒久表现。
由此可见,自古及今,中国文人对艺术中“意”的表现及意之如何去“写”都是非常看重的。
所幸者中国写意精神在绘画艺术中始终得到良好的发展,虽自徐悲鸿始,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继而又因20世纪50年代苏联现实主义的影响,使得美术学院的教学一直循着写实进行,但水墨写意的脉流却一直未断。
写意雕塑的发展却几经波折,因其与绘画不同,绘画由于它平面的特性,决定了其功能性不如雕塑强烈,雕塑的写实主义却易于得到发展,可触可感,可与现实人、事对应的这些特质都决定了雕塑,尤其是写实雕塑易于被大众接受。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如李金发、刘开渠、滑田友等,先后赴西方学习雕塑,基本上继承了欧洲写实的体系,在风格上也颇具西方神韵。他们乃至后来留学苏联的一批写实雕塑家,可以说成了影响中国近现代雕塑的核心人物。
写意雕塑没有堂而皇之进入美术院校课堂,它像顽强的老树被深埋于地下。
(七)从书法角度看写意性
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书法艺术,以出神入化的草书为表达意的手段。文字的象形、会意客观上为书法挥洒自如的写意铺平了基础,从正书到行书再到草书,是离形渐远而达意渐近的过程。草书有法,在法的大范围内,艺术家可任意发挥才能,把握纸张与毛笔接触的瞬间感受,而创造出速度、力度、深度、高度交融,意象万千的书法作品。
三、西方现代雕塑中的写意性
西方艺术在经过漫长的写实主义后,于19世纪后半叶掀起学习东方的风潮,罗丹、毕加索、马蒂斯,尽管文化背景与东方不尽相同,但作为艺术创造,写意能使艺术家直抒胸臆,这一点是相同的。
罗丹(Rodin):通过形体凹凸隐显表达了光影的诗意;当然更表现了人间错综复杂的情感,(注:转引自吴为山《雕琢者说》,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表达了生命的光彩。
马蒂斯(Matisse):在动态和修长的人体中表现生命的快意;形体拉长,快乐的,曲线的。
布朗库西(Brancusi):绝对的几何意念,超尘隔世的意境。
贾克梅蒂(Giacometti):直线式的悲凉,升入天国的理想,与中世纪拉长的造型——只求精神,不求肉体的追求是一致的。
马里诺(Marino Marini):迷恋于雕塑及材料的柔和性,热衷于对母性、大地最原始的情感,饱满、圆润。
亨利摩尔(Henry More):在自然与原始的交织中呼唤精神回归之意。他意象性继承古希腊传统,在其作品《披衣侧卧像》中,衣纹和古希腊建筑“巴特农神庙”在表现手法和意念上有着内在的同构。亨利摩尔揉静穆于浮躁的工业社会,原始、人文被揉进、消化,生发出新的形式,不是裸露的观念,不是生硬的继承。诚然,亨利摩尔是通过“曲解”来体现的。造型艺术发展的根本是形式的发展,形式伴随观念。观念更新带动形式更新。在雕塑艺术中,观念、形式二者是融为一体的,最终呈现的是有意味的形式。
上述简要列举西方现代雕塑作品中的写意性,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写意的形式不同,但总透发出那种朦胧的、神妙的意象,隐隐中看到人性的勃动,情绪的宣泄。
西方的写意重视造型的外形式。他们在理性的千锤百炼中塑就一个精神的实体,就像西方人建造教堂那样,以他们的意志、信仰去构架升向天国的建筑。因此,西方写意雕塑在很大意义上是由“形而上”进入形体塑造的,远离或解构对象,重组一个主观的意象作品。在形态及意念方面均接近抽象。毕加索、布朗库西的作品佐证了这一点。
中国写意雕塑则注重生活的原型,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写意雕塑的理论表现。重视主体对生活对象的感受,并把感受渗进作品。作品的生成往往是急速的,外形呈发散状——区别于“几何化”。另一方面,更注重“神”的写意,集中体现在对瞬间表情的捕捉,并把这种表情理想化、夸张化、诗意化。这在民间泥塑、汉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写意雕塑虽不是作者对着对象写生发意,但处处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热情,因此,在外形方面看不到主观解构对象的痕影,倒是在外部塑造的手法上留下了作者深深的情和意,以及自然的肌理、潜意识中的变形等。齐白石说的比较明确: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这也体现了“中庸”的哲学。
四、中国写意雕塑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角色
上述对东西方写意雕塑进行分析后可看出,虽写意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不得不承认这里有很多共同的因素。人类艺术在高层次是相通的。它也提醒我们:优秀的写意雕塑会为世界所接受并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写意传统的当代性阐释,愈发显示其“现代”魅力,在我们时代乃至以后担当重要的角色。回眸往代,那种产生过强悍写意雕塑的时代本身是具有精神的,是辉煌的。这个时代也是民族值得骄傲的时代。让我们拉开历史的广角来看这个问题。
如前所述,汉代将写意风格推至高端,这与时代有关。春秋以来,居中原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对汉地传统的农耕民族构成强大威胁,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皇帝。到了武帝时期,汉朝军事力量强大,卫青与霍去病两次大败匈奴,汉王朝在两国交锋上占据了主动。卫青与霍去病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公元117年,年仅24岁的霍去病不幸英年早逝,为了纪念他,故修建气势宏大的墓冢,凿石刻。那种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不挠精神从《跃马》、《卧虎》等作品中折射出来。位于四川雅安的东汉石雕《高颐墓辟邪》,昂首挺胸,附阳刻双翼,雄姿威武、豪气冲天,将浪漫的意想与造型夸张的神力相结合,这与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有所不同,它更注重外形的完整性。东汉时的人物雕塑与动物风格雕塑如出一辙。建宁元年时的《李冰像》,浑然质朴,略刻以流畅的阴线,精微处在于祥和、庄重的表情。另一件人物高浮雕《石雕双人像》,刻划男女相爱的场面,没有表情,只有体态、动作。罗丹曾作《永恒的春》,呈现优雅的写实风格。布朗库西作《吻》,展示出神秘的抽象风格。题材相同表现则各异。我曾经将这几件作品做比较来剖析时代精神、地域文化与作品的关系。
再看魏晋南北朝,在民族融合与中外交流的时代大潮下,思想活跃,是最具文化魅力的时期。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影响到社会审美思潮,“轻形重神”的审美观念渗透进了艺术创作,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风格即是受这种观念影响的产物。这时期留存于地上的大型仪卫纪念性石刻,主要是辟邪,神意焕发。
接着,我们再看统一的隋、唐王朝,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空前昌盛。开放的社会使艺术富于想象与创造。唐代的纪念雕刻,体积巨大,并注重群雕在自然环境中的整体气势,在雕塑手法上没有汉代那样自然,也不似魏晋南北朝那样昂扬勃兴的意态,它以深雄的体量和凝练的外型而臻意象,但毕竟在造型上追求圆满。这一点与汉代相比,不免减弱了一些豪气。
……
历史的凝固,启发了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哈佛大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中华文明列为当今决定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的七大文明之一,(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他认为今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尤为显著。尤其是在老庄思想、孔子思想基础上产生的中国艺术亦将对世界艺术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动物风格的写意雕塑、中国的写意绘画及中国接近纯抽象艺术的书法,都必将在世界艺术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当今各种观念艺术或艺术流派,使得很多艺术家在这些风潮中负载太大的压力。一方面要表现自我,另一方面又要找到观众,所以创作时往往受压抑,他们走进写实,被误解为保守主义;他们追求抽象,又失去观众。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处于两极之间的中国写意雕塑提炼生活,凝炼情感,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所疑、所思、所恨、所爱、所感、所悟。因为只有从自己文化血液中流淌的艺术才是自然而不脱节的。如果雕塑家能够将自己多年的架上雕塑或室内雕塑的经验和现代空间环境营造结合在一起,将创造出具有文化深度的作品。
鸦片战争后,门户打开,外来艺术影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新文化运动,再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习苏联模式,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随着现代经济发达,中国进入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生活方式之融通,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得艺术逐渐趋同。文化的多样性、形式的丰富性对人类精神的滋养、栖身起到积极作用,个性的减弱不利于健康的文化生态。因此,在世界建立起独树一帜的中国新文化是客观必然的需要。
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发明可申请专利,推广到世界以驱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艺术则不然,艺术是个性化的——个体的个性——民族的个性,多样并存,反映人类生活、人类思维、人类精神的整合。
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应当看到民族深层心理的宽厚与宏大,要看到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孕育成长起来的文化的优秀性,也要看到写意雕塑到达巅峰的时代,正是完整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时代。文化源流脱节现象的背后是优秀文化的返祖。当今,中国迈向强盛、辉煌的时期,在开放中,在东西方交流的大背景中,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价值,将这种价值置于比较中,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形式的深刻内涵。
当前中国雕塑界有种倾向,以西方潮流为参照。在国际上能博得认同的往往是一些政治波普的作品,形式上已是泛滥了的“国际化”,并不能反映中国的声音。这些作品在中国本土也未曾得到认可,只是西方人站在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眼光选择了在文化上迎合他们的典型而已。这种倾向与文化革命中通过政治题材体现主题而不重视艺术自身规律是一样的可怕。多少艺术家在风潮中迷茫,认不清传统,也看不到现代,最后成为“风头主义”。风头主义活跃,也多新意,但一阵风过后,往往什么都没有。我们呼唤直接从根上长出的新芽。今天乃至未来雕塑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它走向大地天空之间,人们不得不接受。它反映着时代又召唤着时代,写意是中华民族的艺术观,是中国艺术的艺术方法,是迥异于西方的另一个美学体系。写意不是为写意而写意,更不是追求表面颤动、诗意、变形,而是要融化、渗透、张扬精神。有了精神,作品才有了构架,才有了灵魂及内在的“气”,才有了那种一目了然而又意蕴无穷的艺术形式。
一个世纪以来,虽然写意雕塑并没有作为一个概念提出,也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但因为其生命力的强劲,所以,它是不以潮流为转移的。近百年来,无论是游学西方而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艺术家,或是带着中国文化的种子在西方扎根而长成参天大树的艺术家,或是在民间、在本土的艺术家都自觉和不自觉地继承、发展了写意传统,并在此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探索与成就。在此,我们通过对几位华人雕塑家的简析来看这个问题。
熊秉明先生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其父亲熊庆来是一代数学宗师。熊先生师事冯友兰等哲学家,具有扎实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去法国不久,因访问雕塑家纪蒙(Gimond)工作室,看到精严、纯粹、神奇的雕像,认识到“这里不只有大智慧的光芒,虔恪的信念,还弥漫着活泼灵动的生机”(熊秉明语)。之后,熊先生转学雕塑。他把西方谨严的写实和带有哲学般逻辑的三度空间的体面关系对应研究,在体积的塑造中悟出雕塑感的真实内涵。他成功地在中国写意传统文化与西方雕塑精髓之间找到了共同点。他艺术中最典型的我以为是水牛系列。可以看出他是把水牛作为中国大地、作为中国文化来塑造。“既有西方古典雕塑那种凝重、饱满、膨胀的雕塑感,也有中国艺术传统中大方、刚毅、宏阔的雕塑感,中西两个体系的精华因素在朴素的主题中融汇成一个整体。”(注:范迪安《在观念与造型之间》,《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2002年熊先生以八十高龄塑造了一尊长5.5米,高2.7米,宽1.5的《孺子牛》,立于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广场,作为百年南大纪念物,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作品。这头“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地。
台湾雕塑家朱铭,以大斧劈木雕传神写意。早期创作《老子》、《屈原》等人物,气宇非凡,他是放牛娃出身的艺术家,具有浓郁的、顽强的土地情结,后着力于《太极》系列研究,显然受到西方现代雕塑的影响,但由于“太极”题材的底蕴和他早年形成的传统雕塑的写意习性,他的雕塑洋溢着东方的意。
钱绍武先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苏联的一批学子中能将那种纪念碑式的形式,将那种写实手法溶入中国艺术的典型艺术家。钱绍武少时学艺于无锡书画家秦古柳,传统文人的气息影响着他的终身。他的许多作品如《李白》等都借鉴了书法的意韵,只可惜还不够内在,但代表作《李大钊》则具有突破性,它是将传统的写意精神与古朴的装饰风以及纪念碑的永恒性有机结合的经典之作。
此外,从刘焕章、田世信、孙家钵、邢永川、贺中令等雕塑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写意精粹所在。邢永川的《杨虎城》,贺中令的《白山魂》,田世信作品中的纯朴的乡野之风,刘焕章作品中涌动的生命热情等等都昭示写意的洪流还是存在的。著名油画家苏天赐教授深情地写道:
这是一种出现过八卦、老庄、孔子、李白、杜甫……的土地所孕育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气质,这是中华的魂魄。通过艺人的指头嵌入细泥。一代艺人消失了,下一代照样滋生。(注:苏天赐《精神的速写》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放眼未来,写意的前景恰如中国艺术中的虚,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上一篇:中国宋代雕塑史
下一篇:雕塑的发展史
相关推荐